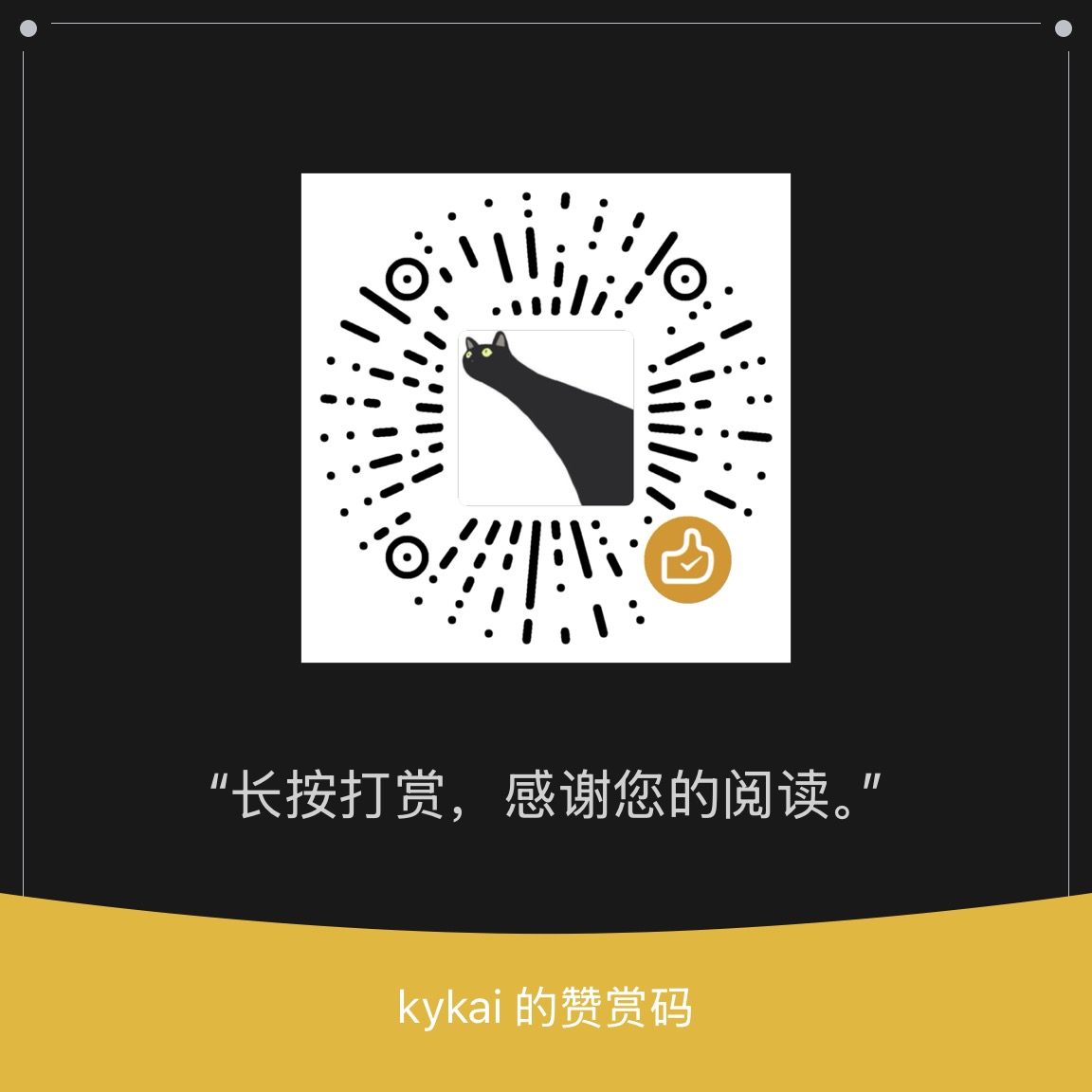在德国,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急诊室,也是第一次夜晚在医院度过。
事情的经过要从头一天的晚上说起。
下了班,我在家旁边的抱石馆运动。场馆里脚臭味弥漫,白色的镁粉飞来飞去。场馆内人员拥挤,占满了通道。我往里走,找到了一片空地。眼前的墙向外倾斜,上面没什么人。我勉强爬了两三米,吊挂在上面没了力气,只好松开手。我没有经验,屁股先摔到了地上,而因为身体反应不及时,仍保持直立,最后腰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
那一瞬间,世界暂停了。等身体恢复了知觉,腰部疼痛到无法呼吸。此刻想起,手里还会紧张到冒汗。我像只蠕虫在地垫上翻滚,耳朵里听到夹杂着德文和英文的关切,脑中一片空白,嘴里呢喃着说着还好还好。但其实并不好,我只不过想避免引人注目,节省出认知资源专心恢复。
躺了一会儿,等身体恢复了,能起身走动,我拖着残破的身子回了家。忍痛洗漱完,躺在床上就掏出手机查各种信息。夜晚伤痛来得急,骨科专科是约不到了,于是赶忙约了个全科诊所,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去查查。放下手机,关了灯,背脊传来阵痛,脑子充斥着杂乱的忧虑。我无法入睡,又打开了手机,歇斯底里地钻进了恶性循环,直到凌晨才昏昏沉沉的睡去。
第二天清晨,我先是去了全科诊所。大夫听了我的经历,简短地查看了状况,直接给了我两个选择,要么吃止疼药回去理疗,要么去急诊进一步检查。我不假思索的选择了后者。握着大夫给的转诊单,我径直坐车来到了家附近的大医院。
兴许是因为上午,医院楼里人不多。一进来就能闻到独属于医院的味道,气氛因此变得大为不同。我顺着指示牌,找到了急诊室入口。那是一扇宽大的磨砂玻璃门,从外面完全看不到里面,大致只有些人影在隐约闪烁。我按了门铃,没怎么等待就开了。急诊室的人同样不多,医护人员看着也很松弛。他们查看了我的转诊单,让我在其中一个房间等待。而后来了一位看着像是印度裔的大夫进来给我诊断。她详细记录了我的状况,并指示我先去拍个 X 光片。
放射科是单独的机构,接受外面的预约同时也和医院合作,后者优先级更高。X 光片的等候室在一个玻璃走廊上,外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,尽头停着急救车。我心想,大概有不少生命垂危的人曾在这里穿梭。
拍过 X 光片,本以为很快看到结果,但他们让我在大厅中等待。大厅中心很空旷,不锈钢椅子靠着周围墙壁。不少老人坐在那里,鲜有年轻人,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殊。大厅周围连接了电梯,还有不少门。时不常有医生和护士出现在大厅,把病患推进急诊室。急诊室的磨砂玻璃门打开瞬间,我朝里面偷偷望去,见有不少病床,还有来回走动的医生。脑子里便生出了很多糟糕的幻想,也许都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。那一刻,我切身体体会到了急诊科医生的辛苦。
大概是忙得差不多了,我被叫了进去。急诊室里喧闹不少,有急救的人,也有被急救的人,乱哄哄的挤在走廊上。除了刚才的女医生,还多了另外一个男医生,我们一起站在急诊走廊的电脑前。他指着我的腰骨片子说:这里有阴影,可能是骨折,需要进一步查 MRI,现在有两个选项,要么自己预约拍片,要么在医院住一晚检查。我不假思索的说了后者,但其实我并没过脑子,以至于纠结是在决定后出现的,但后悔也毫无意义,因此我不得不顺势而为。
我坐到一旁,女医生熟练地给我打了滞留针。瞬时,全徳预演警报响了起来。尖锐的滴答声,从每个人的手机中传出来,回荡在急诊室里。我忽然觉得,警报声和急诊室非常合拍,像某种舞台上的交响,一种特殊的背景旋律,把人们心中的匆忙和疼痛全部描摹了出来。急诊室变得更紧急了。
接过单据,出了急诊室,我上楼找到了住院区。前台的护士问我需要什么,我说要住院,并递上了单据。她愣了愣,旁边凑上来了同事,问我,你医生呢?我说她在忙,让我自己一上来。「哪里有让病人自己一个人上来的?」她们最后这句回复,让我印象深刻。
电话沟通后,护士将我引向 28 号病房。
房间内有四张大床,两个老人正卧床休息。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来自缅甸的护士给我事无巨细地介绍设施。床边有床头柜,旁边矗立着两个支架,一个用来吊点滴,另一个上面挂着仿佛来自上世纪的粗糙平板荧幕,上面有帮助按钮。我脱了鞋,把空空如也的袋子挂在一旁。身子平躺在床,眼睛盯着天花板,新鲜和恍惚。
我知道我有很多时间,却不知能做什么。我无意识间弯曲手臂,滞留的针头搅动着肌肉,无时无刻提醒我在病床上。我刷手机,然后平躺发呆,如此往复下去。
护士每次进来,都会是情绪饱满地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。我问她之后的安排,说有检测可能在明天,听消息就是。到了下午,我才稍感饥饿,餐盘上摆着水煮的西兰花,一些短粗的意面,以及牛肉粒与汤汁。我想到了大学的食堂,那里和这里差不多,总是吃的很凑活,咽下粗糙的食物,全靠能量饮料润滑。看在它们是食物,仍能填饱肚子,我没有抱怨。
医院离家步行只需几分钟。我穿上外套,盖上针头,假借散步的名义回了趟家,拿了充电器和简单的洗漱用品,回去又继续躺在床上。又过了不知几小时,我以为检查会拖到明天,但护士通知说可以拍 MRI 的片子了,于是倍感惊喜,匆忙穿上外套下了楼,等待拍片。
有人说进入核磁共振机,会激发幽闭恐惧。网上评论传来传去,有些人抗拒机器,把它说的和拔牙或做大手术似的。我觉得他们在胡扯,躺在机器上,闭上眼睛,戴上耳机,感受机器把我慢慢推入,感觉天逐渐变暗了。我因为不能动,听觉和触觉变得异常发达。机器的轰鸣声极其有节奏感,听着像 techno。脑子随着节奏,不受控制地飘荡,想到了热情的护士们:西班牙口音的护士,也许是个头头,各项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;缅甸护士,竟然能够说中文,她说自己在餐馆里从云南的老板那里学到的。她语气有能量又温柔,动作也及其麻利迅速,很厉害。
没过十几分钟检查完,我回到病床,看到晚餐很简陋:面包片,猪肉片,酸黄瓜,黄油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,原来晚上即使吃这么少,也有足够的饱腹感。兴许是我只是躺在床上太久,没有任何消耗,但也足以让我反思晚餐是否有必要如此豪华,或说只是单纯的习惯或仪式罢了。
窗外渐暗,白天值班的护士和我们道别,又迎来了一批值夜班。有两位比我还小的年轻人,看着还在实习,说要给我打抗血凝针。听到要打针我慌了神,想要推脱。他们同我耐心解释,说是医生授意,一定要打。我知道自己拗不过他们,因此就认怂了。年龄更小的男生显然将我作为实验的对象,在我肚子上扎针,手法算不上利索,但万幸没引起我更大的疼痛。
仿佛两个世界,病房的夜晚极其特殊,与平常的大不相同。我本以为夜晚的休息是对病人最好的疗愈,但其实却是痛苦的开端。
我手表没了电,也就没太在意时间,用余光瞟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病房里的没有全黑,几盏小射灯仍能照出轮廓。除了我以外,还有两个老头,一个在侧边,一个在斜对面。他们都病的很重,似乎刚经历过巨大的手术,躺在那里蔫蔫的,也几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活动。止疼泵同他们的身体相连,各种检测仪器以错落的频率闪烁出不同颜色的光芒,同时发出富有节律的滴滴声。每过一段时间,不知什么地方的机器还会响起低沉的轰鸣声。
我恍惚的半醒半睡,觉得窗外有人在放烟花,于是朝着小窗外望去。墙壁遮挡了视线,我只看到窗边的一侧有些色彩缤纷的倒影,同时也听到了轰鸣声。想到了句歌词,「看著窗外的光,分不清是路燈還是太陽」。我好奇,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?城市中在庆祝什么?我们身处在另外一个世界空间动弹不得,仅能靠微弱的感官,去感受那个世界发生的事情。这个世界不会发生人类的共有。想到这些,我感觉到一丝落寞,于是挪了挪身子,尝试继续入睡。
也许是夜晚太安静了,人的感官会被过度放大,因此痛苦也会。约莫过了零点,耳边传来了他们沉重的呻吟声。起初我并没有太过在意,想着有止疼泵的情况下,应该能帮助到他们,但随着操作止疼泵的咔哒声频繁响起,呻吟声反而变得越来越大,最后成了嘶吼。还能隐约识别到一些脏话,但词汇因为嘶吼的关系变得异常模糊。斜对面的老人叫的最为凄厉,持续的发声使他的嗓子嘶哑,即便如此,声音还在不断的持续。凌晨,护士曾来帮助过他一次,但也许是夜太深,他的痛苦并没因此而缓解。叫着叫着,直到后半夜,他失去了所有的力气,只能发出轻微的哼唧。病房再次沉寂下来,只留下机器在运作,我也能得以在恍惚中睡去。
这样度过了一个相当难熬的夜晚。第二天清晨,缅甸的护士来上早班,又用极富激情的语气呼唤我们起床。白天的光透过窗户,照亮了病房,直接冲散了夜晚沉重的气氛。早餐是面包,奶酪,还有咖啡。不得不说,医院里的咖啡感觉更好喝,温和又提神。
我简单打理后,靠在床上发呆。斜对面的老头状态明显好了许多。他几乎没法活动,因此吃喝拉撒都需要护士的帮助。我看到护士将被子掀开,把宽大的,本质上就是前后两块布的手术服掀了起来,下面垫好像是一次性纸尿裤的东西,让他能顺利的排泄。结束后,护士利索地清理了现场,走进卫生间将排泄物给清理掉。整个过程极其专业且迅速,看得出来,她们已经做过太多次了。
一方面,我感慨做护士或护工的辛苦,难怪类似岗位在德国需求量巨大。工作收入不高,却又脏又累,同时还要保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,不是菩萨做不来。另一方面我想到,用机器人取代真人是种糟糕的设想。技术一定会越来会好,在未来,机器人也确实有能力取代真人,但问题在于,这种设想来自于「健康人」,而不来自于「病人」。病人能做的,只能被动的接受,而决定不了对方是暖的还是冷的。相比技术进步,我更相信大部分的有钱有势的,会让真实的人类帮助他,而不是机器。
还有个感慨是,人应该要终身保持锻炼与运动。之前没经历,只觉得运动是个精神泵,能让人精力充沛,充满活力就足够了。现在经历过了伤痛,体会到了它对身体物理方面的重要性。肌肉,筋,骨骼,神经等等,无时无刻的都会因为运动而受益,一旦它们强壮了,即便是年龄大了,身体机能降低,仍能帮助我们抵抗外部的各种风险。我希望在自己老的时候,身体还有能力去支撑我完成必要的动作,而不是全身脆弱,充满各种伤痛。
吃过早餐,医生开始绕着整个病房巡视。如同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,一个稍微年长的医生打头阵,后面各种年轻的医生则跟在后面。进了病房,他们挨个巡诊,我是最后一个被转到的。
看上去十分资深的女医生,先用德语和我解释检查的结果。我担心自己理解有误,所以又请她重新用英文解释了一遍。当然,「请」这个表达背后包含了很多勇气,尤其是看到她身后的年轻医生们拿着纸笔一边听一边记。我也不清楚,像我这种外国人是不是也会作为特殊的案例被他们收录进经验里。总而言之,最后诊断的结果算不上很糟。虽然腰部有压缩性骨折的情况,但万幸骨头没有移位,意味着不需要做手术或安装支架,只需要静养就可以。医生同时还强调,最起码六个星期内,不要做任何运动以及做任何需要腰的活动。
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令人焦虑的信息,医生的结论和建议让我释然了。我收拾东西临走前,医生把报告交给了我,还特地的嘱咐说,好好休息,不要去谷歌任何的信息,如果情况恶化了,直接来急诊室就是了。听完,我觉得无比安心。
我走出病房,找到护士长,让她把我的预留针取出来,最后用磕绊的德语,十分用力地感谢她们的照顾和鼓励。等电梯的时候,我撇到有不少老人从病房里被推出来,又听到因痛苦而声嘶力竭的尖锐叫声,依旧在楼道深处回荡。
我走出医院的大门,感觉通过了一道生与死的结界。结界的里侧是伤痛与死亡,外侧则是生机与希望。而细腻的温情和爱是少有能够跨过这道结界的虹光。